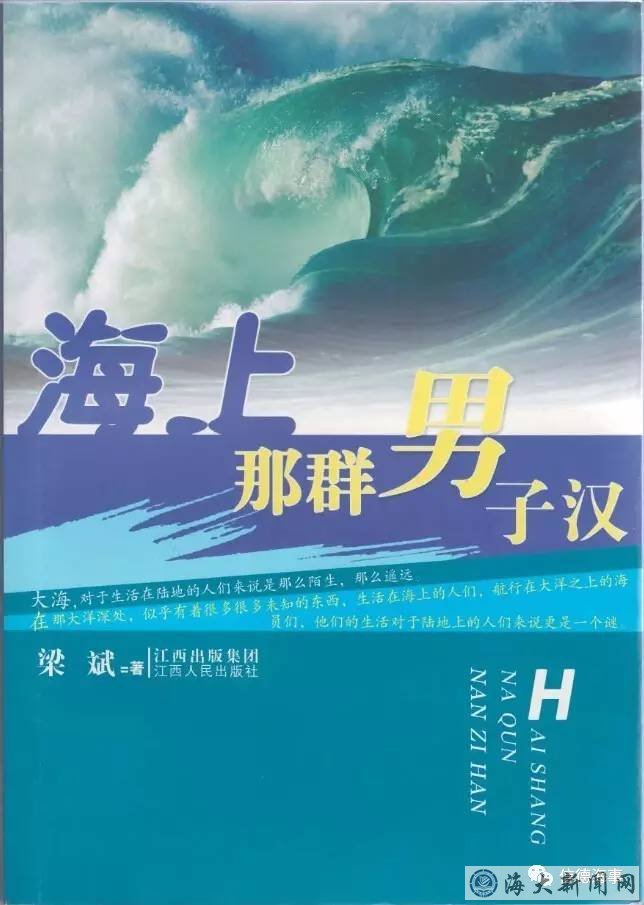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和我不太熟的朋友问我:“你们海员老到国外,一定有不少花花事吧?”如果我断然否认,不仅人家不会信,我也底气不足,这个问题不可能回避,我只能实话实说。
长时间的海上生活,枯燥无味.世界上的事大多是两方面组成的,有阴就有阳,有男就得有女,失去了平衡,违反了自然界的规律,准会出事.可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当年中国远洋海员们是怎么度过没有异性的日子而不犯”错误”的.我知道有一见女人就眼睛发光的,有偷着看黄色电视节目的,就是没听说过在国外逛妓院的.在有些国家,妓女们就像展览品站在大街旁的橱窗里让人像挑商品一样选.在这些地方,一旦有中国海员的身影,顶多是远远地看一眼转身就走.
是因为没有钱?不是,我马上要讲的故事可以否定这个理由.
是因为品德高尚?不一定,我们都是凡人,有血有肉,而且个个年青力壮,那能没有欲望.先讲个笑话:一个远洋海员远航十个月后回家了.老婆一见面就逗他:”哟呵!挣钱的英雄汉回来啦?急的够呛吧?是先上床还是先吃饭?”
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说的海员们都那么”乖”.我也解释不了是什么使我们就这么”老实”.还是讲真实的故事吧.
80年代末的一个秋日,一艘远洋货轮靠上了美国佛罗里达洲的坦帕港装化肥。
这条船上,高级船员有欧洲人和香港人,普通船员都是来自中国的年青海员。
这天晚饭后,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停在了船边,车上下来了两个年青漂亮的中国姑娘,她们大方地上船询问:“这条船上的大陆船员在么?我们是在本地留学的台湾留学生。”
中国海员们听说来了两个台湾女留学生,大家都聚集到餐厅,拿出茶水,果汁,水果招待同胞。
一般这种场合,都是因为当时台湾人不了解大陆,来找大陆人聊天,想知道些大陆人生活的真相。大家不过坐在一块聊聊。可今天似乎不大对劲,这两个姑娘坐在中间,不断地说:“我们是学生,想必你们这些常年离家的男人会有很多事需要女人做,就上来看看能不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两人一边说还一边对着男人们送出挑逗的媚眼。
大家奇怪了?这是什么意思?妓女?不像呀!
两人看大家都没反映,接着说:“听说大陆管得很严,和妻子之外的女人睡觉是要坐牢的,如果是女人自愿的也犯纪律么?”
正在这时,香港二副进来了,他一看如此如花似玉的两个姑娘,色眼一下眯了起来:“好耶好耶,靓妹到我屋去坐啦!我们玩玩啦!“
两个姑娘很生气地说:“不去,我们是来找大陆阿哥的,不和你玩!“
中国海员中几个岁数大的悄悄互相使了个眼色,溜出了餐厅。他们聚集在走廊上商量:“是不是这两个姑娘没钱交学费或生活费了,跑到这来卖,这样卖她们的台湾老乡不知道?不怕毁了名声?”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分头去做事。
一会儿,他们把两个纸箱放在姑娘们面前:“我们的工资低你们也知道,没钱帮助你们,这些是些吃的和生活用品,一点心意而已,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我们给你们搬到车上去好么。”
两个姑娘你看我我看你,一副无可奈何的样:“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我们不漂亮?你们不需要女人?如果我们自愿的,不收钱你们也不行?”
年龄最大的水手长向她们解释,大陆船员有纪律不假,但我们还有一个要对得起自己妻子的自律。
两个姑娘看看没戏了,垂头丧气地站起来要走,大家要搬东西,她们坚决拒绝,甚至有些动怒的说:“不要,我们什么都不缺!气死我们了!真不明白你们大陆人是怎么回事!”
两人钻进车一溜烟地跑了,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傻爷们百思不解。
第二天晚饭前,又一辆小卡车停在船边,车上下来四个中国男青年:“大陆兄弟!快来搬酒和好吃的,我们来和你们庆祝了!”
原来这四个也是在本地留学的台湾学生,他们和中国海员们嘻嘻哈哈地把东西搬到餐厅,大家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天,英国船长听说了,特地破例来到普通船员餐厅,为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相聚干杯。
大家喝了一阵后,有人说起昨晚的事,觉得那两个姑娘很奇怪。
四个台湾男学生互相挤眼睛,哈哈大笑:“她们是我们的同学,是这么回事。昨天晚饭时我们凑在一起聊天,有人从报纸上看到港口来了条船,船上有大陆海员的报道。就说起了大陆不能搞女人的事,她们两个不相信,说是没有不吃腥的猫,没有不花心的男人,在海上时间那么长,正常的男人谁也受不了没女人的日子,就算没钱搞或者是有纪律,如果是女人是自愿的,不要钱,那个男人能不干?于是她们就和我们打赌,如果她们回去拿出证据大陆人和她们睡了,我们负责她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并给她们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如果输了,她们这个月给我们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哈哈!昨晚她们回去,认输了!”
海员们说欧洲的漂亮姑娘在三个地方:法国马赛,西班牙巴塞罗那,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康斯坦察的姑娘确实很漂亮,她们除了具有白种人的高个子,长腿,金发,蓝眼和丰满的身材,还有白白的皮肤。一般白种人的皮肤虽然白,但细看有很多雀斑,还很粗糙。而康斯坦察的姑娘也许是生活在海边吧,皮肤白净细腻。一个个像奶油捏的洋娃娃。
船在康斯坦察时,一天上午我和水手在甲板上值班,船下的码头上一群女工在整理棚布,因为是冬天,她们捂的严严实实的。水手是刚从海校毕业的小伙子,他说女工里没一个年青的,我说:“不对,那个拿着本子的统计员就是年青的,我们俩打赌,要是我说对了,你就把口袋里的“肯特”牌香烟输给我,反之我就输给你我的“555”烟。“
我们俩走下船到女工们中。我对那位统计员说“你会说英语么?”
她拉下脸上的口罩露出一张年青,漂亮的脸:“当然会。”
“你能摘下你的帽子么?”
“OK!”她摘下头上的连衣风帽,露出一头长长的金发,果然是一个漂亮的年青女郎。
我乐哈哈的一把从水手口袋里抓出烟,没等装进我的口袋,那些大姐们一拥而上抢了个精光,罗马尼亚进口货少,外国香烟很受欢迎。
可金发女郎不干了:“你们好像是拿我说什么事?”
“对不起!”我对她讲了我和水手打的赌。
她哈哈大笑起来,“那就不给我点奖品?”
我从口袋里拿出三五烟递给她,她高兴的接过去“谢谢!我留给我亲爱的米哈依抽。“
第二天上午,我去城里路过仓库,统计员从仓库里她的办公室窗口看见我,敲着窗子叫我进去,我正好想问问城里最好的商店在那,就走了进去,里面有她和另外一位上了岁数的大姐。她很羞怯的问我:“你能给我些中国的大白兔奶糖么?“说着她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我的宝宝萨萨。五岁了。“
“好可爱的小伙子!好吧,等我从城里回来我给你送来。“我慷慨的答应了。问了问我想知道的地方怎么走,我就告辞了。
下午我拿了些糖果走进她的办公室,那位大姐一看我来,站起来向外走,我一边向她问好,一边递给她一块巧克力糖,她接过我手里的巧克力糖冲我坏坏的一笑就出去了。
她坐在桌旁,一头披肩的金色长发微微地有些卷曲,瓜子脸下巴却很圆润,白净的脸上只有几狸雀斑,显得有些俏皮,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下是直直的鼻梁,嘴唇上淡淡地抹了些口红,上身穿着一件紧身毛衣,下面是一双毛料西裤裹着的修长的腿,苗条的身材一点不似那些生育过的女性,腰细细的,高耸的胸部挺立在毛衣下。我俩聊了起来,她叫安娜,英语是自学的,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了,和中国海员打交道不多.她问我从中国航行到这要多少天,过那些海区,海上风浪大不大,我本来坐在她对面,聊着聊着,我在她放在桌上的纸上画从中国到这来的线路。她把头凑过来听,我闻到一股香味,那不是香水味,而是女性的体香,我转头看着安娜,安娜也抬起头来看着我。她蓝蓝的眼睛像一汪湖水,闪闪发光,没抹口红的嘴唇微微的张开,长时间的海上生活憋在我身上的男性力量併发而出,我低下头一把抱住她吻了起来。她并不反抗,反而紧紧的贴过来。
许久后,安娜把头向后靠了靠,用眼向我示意,屋里有一张床。我猛然冷静下来,放开安娜摇了摇头。
安娜迷惑不解:“为什么?“
“不,我们有纪律,如果我和你做爱,回中国我会被“我做了一个戴手铐的姿势。
安娜挣大了那双蓝眼:“怎么会?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中国的有些事我无法对你解释,对不起!“我转身出了房间回船了。按当时我们的纪律,我单人下船就已经违反规定,我再也没有找过安娜。
要说中国远洋船上的纪律,那可是多如牛毛,但不准搞风流事这是铁板钉钉的一条,不要说嫖了,以前和外国女人说几句话船上都会有人当回事汇报到上级那。比我们老的海员们几乎没听说过有人犯过这方面的错儿。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就是怕犯纪律也不能解释的通,毕竟我们语言通,敢跑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活动。
几天后,我们船移码头要离开,在船上,靠离码头作业时,大付在船头,二付在船尾,三付在驾驶台协助船长。我站在驾驶台正干着我该干的事,只见安娜从仓库里走了出来,她看见我们船离开,就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一看,躲进驾驶室内。
转靠好码头,中午吃饭时,水手们纷纷议论
“刚才那漂亮的金发妞是咋回事?先到我们船尾找驾驶员,看见二付她又说不是,跑到你们船头去了。“
“是呀!她跑到船头来,看了看大付也说不是,这会船也离的远了,她站在下面还抹眼泪哪。
作者简介:
梁斌 男
1958年出生.北京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延庆县插队. 后进入北京铁路分局工作,任铁路工人.
1977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计算机专业,后转入78级航海系远洋驾驶专业学习.
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工作,任远洋货船驾驶员.远洋货船一级大副.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1991年转到陆地工作,从事过多种职业.
2002年开始写作,曾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其纪实作品集《海上那群男子汉》已于2008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创办网络广播《海事船说》,并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FM等平台发布相关作品.该广播内容为音频版《海上那群男子汉》、《海院走出的男子汉》以及梁斌先生主讲的“世界海战史”脱口秀等节目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