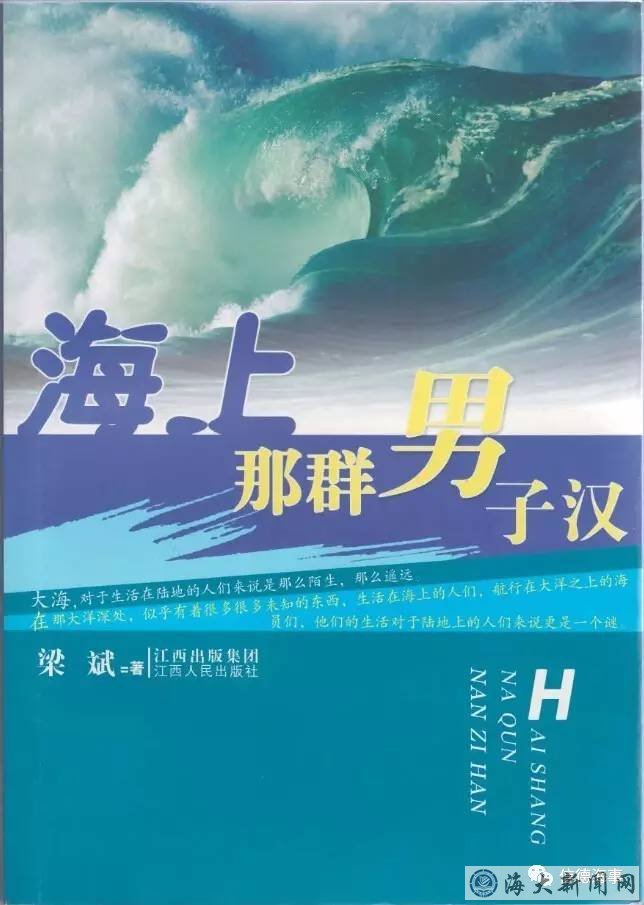
电报主任老刘是天津人,听他讲故事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可以把一段经历娓娓道来,听得人如身临其境。
1978年的秋天,我在“武胜山“轮作电报员,那是一艘载重吨6700吨的杂货船,1959年西德建造,船上有38名船员,主要航行于东南亚沿海各国,为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服务。
那年,越南在结束了抗美救国战争,南北方统一后,为了实现它的大印度支那梦,派谴数十万大军入侵柬埔寨,战火在饱受长年战乱,刚刚得到喘息的柬埔寨国土上又一次无情地燃烧起来。越军凭着二十年的战争经验和美国留下的大批军火对付人少力单的柬埔寨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柬埔寨的部分国土,一路向南杀来。
“国庆节”前夕,我轮接到的公司命令:从湛江港装运援柬物资去磅狲港卸货。
磅狲港,原称西哈努克港,位于暹逻湾(亦称泰国湾)的东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即是重要的商港,又是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从这可向北航向泰国,向南进入南中国海,可航向新加坡,进而袭扰重要的海上要道马六甲海峡。从以前去过那的老水手口中,我得知那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港口,由于地处亚热带,那里物产丰富,人们性格善良,出产用不完的鱼米水果。商业也很发达,有很多华人,有的已在那生活了几代,很多人成为当地的富商,由于西哈努克国王和我国有良好的关系,那的人对中国人很友好。但自从郎若-施里玛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王国政府投靠美国后,就再没有中国船去过那。红色高棉推翻卖国政府夺得政权后,中国船才开始去那里。
开航后,根据上级通报的情况,船上做了些准备,船艏,船艉,驾驶台顶部各装上一挺14。7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每个船员都配备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全体船员组成高射机枪,救护,消防,通讯,堵漏组。全部按民兵要求置于船长,政委的指挥下。并进行了几次演习,我们船上60%是转业军人,对于去战区,我们这些当过兵的并不觉得可怕,甚至有点兴奋,当兵就得打战。那几年,听说我们有部队入越作战,我们没赶上,当了几年和平兵,转到这商船上,可能还能碰上真枪真炮的干一下,补补没打过战的遗憾。再说那地方那么美,有的伙计还准备好了各种渔具,打算到港好好钓点鱼吃。
可从上级通报的情况来看,有军事常识的我不禁有些疑惑,虽说越军武器好,人多,可柬埔寨解放军也是拥有一国资源,又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影响,打的是反侵略战争,再不济,用游击战与敌周旋也不至于退的如此快呀?我也是瞎操心,还是到那看看吧。
我轮经过5昼夜的全速航行,抵达磅荪港外引水猫地,抛锚等待柬埔寨引水员引领我轮进港。按照国际惯例,一国船舶抵达另一主权国家港口时,应在该国指定的港外水域抛锚,等待该国派出的引水员登船引领进港,这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也是因为引水员都是资深船长,对当地水文,航道等情况了如指掌。
当港口送引水员的拖轮靠拢我船时,拖轮上站着七八个人,他们着清一色的服装。头上是中式的草绿色解放帽,一身黑色衣裤,脖子上围着印着小格子的,当地人叫汗巾的长围巾,脚蹬用汽车轮胎做的凉鞋。其中两人携带“54”式手枪,其余的持“56”式冲锋枪。船长看到他们携带武器,便用英语问他们是什么人,对方回答是引水员,船长疑虑中先指令水手放他们上船,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上驾驶台后,带手枪的一位岁数稍大些的人向船长做了解释:在柬埔寨,全国施行军事化,全民皆兵,引水员也不例外,他们既是港口工作人员,也是军人。带手枪的是引水员,持冲锋枪的是警卫人员。我们船就在这些武装引水的“押解”下,驶进了磅荪港。
靠上码头后,柬方开始卸货了。从停在码头边上的十几辆“解放”牌大卡车上跳下一群十七八岁的年青人登上我轮卸货,他们和引水员的装束一样,只是没带武器,看来也是军人。由于他们在船上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想这些军人接触,柬埔寨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英语在这行不通,但这儿应该有不少的华人,可我们用中国话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只是裂嘴对我们笑一笑,没什么反应。我们船员中也有很多广东人,福建人试着用方言和他们沟通,也是徒劳。是不愿说还是真不懂?我们搞不清楚,好在柬方派了一个翻译和我们沟通。工作上的事还没问题。
由于安全考虑加上越军的飞机经常来侦察,卸货都是在夜间进行,岸上没有电,码头的卸货设备不能用,所以,卸货全部用船上的设备工作。其实就是有电,我看岸上那些设备也是年久失修用不上。白天不卸货了,我们就三三俩俩的下地去逛。
港外的城市已是破烂不堪,没什么看头。倒是我们跟着完成了工作的军人后面,走到了他们的军营。那是一排排的草棚,用竹子和木头搭的架子,外面苫着芭蕉叶或茅草,分成三区,一区男兵住,一区女兵住,还有领导的草棚和伙房,位置分布的很得当。就是第三区有点让人看不懂,棚子不多,就几个,和主区分开。里面有人住过的迹象,但白天没人进里面。
游逛中我还发现,人们走路和我们都不一样,不是按行进方向走,而是分男女,男人走一边,女人走一边,真有意思。
靠码头的第二天,我们船上的一个同志病了,连续高烧不退,船上医疗条件有限。船长和代理联络要求到陆地医院治疗,船舶代理就是当地的人受船公司的雇请,代表船方处理与港口等陆地有关方面关系的代表。在这当然又是军人。代理说只能到首都金边医院,那里有中国医疗队,可以派车送我们去,安全不成问题。领导研究后决定派我,政委,政干(船上的保卫干事)医生陪那个病号去,再说在那还有我们的使馆,我政委还要去汇报工作,请示一些事情。我们担心一路上语言不通,可翻译对我们一笑:司机会中国话。
第二天一大早,开来了两辆白色的美国产福特轿车,停在船边等我们上路。我们几个人赶忙放下饭碗,扶着病人下船,我们走到车旁边,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正在擦洗汽车,他们停下手为我们打开车门,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坐到车上后,我们东张西望找司机,没想到俩个孩子收了水桶分别大模大样的坐在司机的座位上发动了车!
政委赶忙说:“你们别玩车,让司机来开。”
孩子对政委一笑,用不太流利的广东普通话说:“我就是司机啦!”
我们惊讶的面面相觑,眼前这个孩子身高只有一米六,黑黑瘦瘦的,体重不过百斤,在中国也就刚上中学,柬方派这样俩个孩子驾车送我们去金边?行不行呀?可从孩子发动车,娴熟的把车调头驶离船边的操作。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老司机。
车在孩子熟练的驾驶下,驶出了港口,上了通往金边的四号公路,此时我们的不安和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政委和男孩聊了起来。
“你会说中国话?是华人吧?”
“我是柬籍华人,听阿爸阿妈说,我的爷爷是中国的潮洲人,很早以前下南洋到的这里, 我的祖母是柬埔寨人,我阿爸阿妈也出生在这里。”男孩很健谈。
“你多大了?”
“13岁啦!”
“开车多长时间了?”
“我从10岁就会开车了。”语气中透出一种自信。
我们不越而同的交换了一下惊讶的眼神。
“你这么小就开车,你家里人就不管你?”
孩子的表情有些异样,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阿爸阿妈打仗打死了。”
“你家里还有其他人么?”
“有一个哥哥去年参军了,听说现在在北边和越南人打战,还有一个妹妹在女营。““比你还小的妹妹在女营?”政委惊奇的问。
“哦!你们不知道啦,我们柬埔寨有男营和女营,就是男人和男人住在一起,叫男营。女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叫女营,大家都是兵啦,男人和女人是不能住在一起的,否则会杀头的。”
我想起了看到的草棚军营,就插了一句话:“夫妻也分开么?“问完我有点后悔,这样的事问一个孩子不合适。没想到男孩说的很详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可以申请结婚,只要向领导申请,领导就会根据申请人数的情况,在某一天傍晚将申请结婚的人按男女排成两排,对面站好,站到你对面的人就是你的妻子或丈夫,一对男女分给一个棚子过他们的洞房之夜,三天后,各人各回自己的营,每个月,结过婚的人可以申请夫妻团聚,领导根据申请人的表现,批准给一到两夜的假。
我这下明白了那个特殊的草棚区是做什么用了。
“你也是军人?当兵几年了?”政委又问。
男孩仰起脸,骄傲的说“当然是啦!我都当兵三年了。“边说边得意的拍拍腰间的五四”手枪,表示他说的是真的,并回头冲坐在后面的我们天真的一笑。
我们也笑了,但笑的很勉强。
一路上,车开的很慢,主要是道路坑洼不平,四号公路原来是沥青路面,被炮火炸过后,路面上弹坑累累,虽然经过简单的土石修补,但没有压平,也没补沥青,车行驶在上面颠簸很厉害。沿途的河流很多,从磅荪到金边大约要经过十几座桥梁,但全部的跨河公路桥都被炮火摧毁,过河只能小心翼翼的走河面上架设的舟桥。而且四号公路沿途俩侧的山上,大部分山顶有明显的被炮火和炸弹轰击过的痕迹,从山脚到山坡间的绿色植被完好,而接近山顶的树木和植被却残断焦黑,看上去像大火烧过,山顶光秃秃的,山石和红色的泥土像被犁翻过一样,想像得出当时的战况激烈和残酷。
将近中午时,车的右后胎忽然爆裂了,男孩立刻将车停在路边,钻出驾驶室查看破损的轮胎。我们也都下了车,一面等男孩换胎,一面活动活动坐酸了的身躯。我想看看这位老司机要多少时间换个轮胎,就特意记下了手表上的时间,男孩打开后备箱,取出备用胎,工具,我看他搬轮胎时很吃力,便上前想助他一臂之力,被他拒绝了。他先用千斤顶将车抬起,然后飞快的用扳手卸下破胎换上新胎,用脚踹了踹换好的胎,满意的点点头,又将换下的轮胎搬进后备箱,我看了看表:7分钟!真是一个熟练的老司机,我不由的以敬佩,同情的目光看着用汗巾擦着满头汗水的男孩,他裹在黑色衣衫下的身材是那样的瘦小,我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岁数,他应该坐在宽畅明亮的教室听课,学习文化知识,应该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撒撒娇,应该和伙伴们玩,应该跟在父亲后面去打球,游泳,应该...
哎!战争改变了本该有的一切,也改变了孩子们的童年,使他们过早的接受了战争这个残酷的现实。
又上路了,我发觉公路上隔不远就有由军人把守的检查哨,过往的车辆都要停车接受检查。而我们的车却一路从不停车,哨兵不但不阻拦,还主动指挥其它车辆为我们让路。我们问男孩这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车是白色的,在柬埔寨,白色的车都是政府官员和外宾用车。
下午我们到达金边市郊,路过波成东机场时,战争遗留下的痕迹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这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整个机场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路边的里程碑弹痕累累,已看不清碑上的公里标识。残存的墙壁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弹坑,路边的树木大部分被炸断或烧焦。眼前这满目的战争苍痍,使我们刚刚松下来的心情,又收紧了。
作者简介:
梁斌 男
1958年出生.北京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延庆县插队. 后进入北京铁路分局工作,任铁路工人.
1977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计算机专业,后转入78级航海系远洋驾驶专业学习.
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工作,任远洋货船驾驶员.远洋货船一级大副.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1991年转到陆地工作,从事过多种职业.
2002年开始写作,曾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其纪实作品集《海上那群男子汉》已于2008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创办网络广播《海事船说》,并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FM等平台发布相关作品.该广播内容为音频版《海上那群男子汉》、《海院走出的男子汉》以及梁斌先生主讲的“世界海战史”脱口秀等节目作品.

